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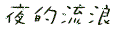

拌合機前
拌合機的承載斗又放下來了,我們接過一包水泥,拆線、抖開,澀灰的水泥滾入,細沙發進去,粗石跳進去,引擎隆隆啟動,沒有休歇,只要三包水泥,十二籮沙石,拌合機的承載斗又昇上去了。
滾筒轉動著,八桶水和了進去。滾筒轉動著,太陽照射著。
還好只有八百包水泥,最多晚上八點半可以完工。
我們要灌出一道厚二公尺的擋士牆,然後回去,吃點心,到明晨起某號響時,最少還有八個半小時的休息和睡眠。

小港
群鴿飛起的清晨,泥潦的小港,水澤正慢慢退了下去。從這村子的埡口,可以看得到潮起的海,和那些游移的船隻,過來就是港了,還有工業區的煙囪和城市的塵灰互別苗頭。
傘兵部隊的機群向更遠的南方進擊,陽光從崗哨的口徑穿入,睡夢中醒來的衛兵,慌張著向一列扛著圓鍬的工兵行禮。

在斗六車站,午夜
有人躺在長凳上睡覺,計程車司機的吼叫從出口一路排到小攤圍起的廣場,一個少女在售票處詢問南下火車到達,最正確的時間,並且低下焦燥的臉,用希望和愛情安撫她左手上的腕錶。
火車慢點,這麼深的夜晚。

至於小琉球
至於小琉球,除了三名冰果室的少女,我們恐怕沒有留下多少。
海浪,甲板,微腥的風,啟動的馬達。各種人,旅遊或者回家,這樣一條船。三名大兵,三張眼前嬌柔的少女的臉孔,在船首談笑,並且決定到小琉球的海灘上烤魚。
後來我們之中,只有B釣到一尾魚,回到陸地後,這尾魚又溜走了。
這是邂逅,可笑而無奈,驚心不動魄的小琉球。

北上列車
那少女,二十一歲左右吧,十分成熟、美麗,唯一遺憾的是,她的嗓子不好,說起譯庲粗聲而令人不適。
先前她在我旁邊坐下,微笑,且讓我感覺出一種溫暖。後來她問我是不是在當兵,我竟有些不快,但還是點頭,於正她談起伊在海軍陸戰隊服役的弟弟,黝黑、健壯,而且剛升下士呢!這位小弟,你呢?上兵,我簡單答覆,於是她相信我比伊二十歲的弟弟還小,因為她最會猜人家的年齡了,而且還亂靈的呢!我嗯了一聲,於是她又開始談及伊弟弟的高中女友,並且相信我一定而且要有女朋友,這女朋友一定而且要是低於伊弟弟的女朋友一個年級的高中女生,我努力給她最有禮的一笑,於是……
於是我睡著了。醒來時,車過中壢。一個細柔而怯弱的聲音問我,是不是在當兵?我驚極而喜,並盡力用最委婉的態度來肯定。當兵好嗎?嬌弱的聲音問。當然,聲音沉默下來。妳有弟弟嗎?弟弟不是在陸戰隊服役嗎?聲音羞怯著。妳弟弟剛升下士,而且一定有個高中女友吧?妳看,我猜得多準,不是蓋的。聲音不答。但我感覺到一種冷峻的拒絕。
我別過頭來。
一雙驚訝而不解的眼光,粗糙的面頰,因抽煙而微帶褐斑的不整齊的牙齒,整個下巴濃黑的鬍鬚。
世界變動得真快!我趕緊遞給三十出頭的他一根國光煙,並且向他提起高速公路和電化火車來。

演習場的暮雨
我們在傍晚時刻抵達湖濱小村,整個天空忽然陰霾起來。
雨先從湖中落起,然後衝鋒到了湖濱的村道,再來就滾進到整齊劃一的天主教墓園了。
我們的駐區,緊臨著墓園,在所有兵士獲得解脫的眼光抵達時,也下起雨來。

關渡和歷史系的朋友
乘火車來到這個小站,歷史系畢業的他已站在出口等著我們。
斜陽剛睜出火辣的眼光來,我們迎著陽光走去,只微微看到他的臉型和一副墨色的眼鏡。兩名少女,一位是我的大眾傳播系的女友,她們的好奇,我可以從耳邊感覺。
他失業一年了,剛學會開車,我問他考執照了沒有。走進大度路時,一輛計程車,載著香客而過,想到日後他也駕著計程車,我勸他在車內貼現代詩,而不是「請勿吸煙,冷氣開放中」什麼的,要不就放一本台灣通史吧!關渡在第幾頁?
地道中,或者不如說是洞窟中,很多金碧輝煌的神像,關於金碧輝煌,是另一位歷史系肆業的女孩說的。最好都保持原色,黑,我說。歷史本來如此,輝煌應該留在後輩子孫的心裡去體會。
淡水河在下,觀音山在前,海風很大,我們站在香火鼎盛的廟前,望著渡口,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

鐵道旁的溪流
火車嗚地一聲,通過了烏鬱的山洞。
淡水河斜斜地從窗口衝到我們眼前來,包括河邊一名釣者疾速拉起的鉤和線,也甩過我們微霎的睫毛。
鐵道些微彎曲地走向台北,秋天的陽光,黃昏裡顯得十分脆弱,恰好可以用來當成妳髮上的羅巾。
沿著妳金鬱的髮波看過去,一行白色的帆船,參差有致地,像雁子一樣,遲緩地通過。
妳在我的驚嘆中轉過頭去時,所有金黃的髮浪正好淹覆了白帆和鐵道,還有鐵道旁的溪流。

在燕巢的夏天
在燕巢的夏天清晨,每天早上醒來,我照例先抽一根煙,潤喉吧!或者是漱口?
有時碰巧遇到跑步,部隊答數跑著通過營區,沿著阿公店水庫外圍,在晨霧微曦中,最能體會山明水秀的壓迫和擁擠了。
但煙是如何也不知要戒了,半是習慣,半是寧可強烈感覺山水的迫擠和衝撞。

流浪樹
有一種樹,就叫流浪樹,像候鳥一樣,隨著季節變遷,會自行移植到適合紮根生長的地方。
這種樹的葉子,在春天時鮮明青綠,秋天時金黃而有流光,夏天他要在北地的山巔,冬天他選擇南方的海岸。葉子落了,就落在根上成為根的養料;根鬚刺探著,又成為葉子仰望的眼睛,不長花,但是結果,每一顆果實上都展示出他的面顏和心境。
土地是他的歸宿,但他沒有固定的家園,流浪似乎是他的命數,而這命數又終要歸結到他離不開的鄉土。
有一種樹,就叫流浪樹,他隨時在移植播遷,尋找愛情,像候鳥一樣,他的翅膀飛過天空,他的根蒂,愛恨交加地擁抱著整個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