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燈火漸暗的夜裡,重讀發表在《中外文學》的〈我的姓氏〉,我忽然感覺「A-Wu」彷彿就在燈光照不到的暗處,問我:你寫的是我嗎?而不敢確定這樣的書寫,是在填補我自以為是的認同的隙縫?或者,是在強化隙縫的認同?
|
|

.................................
向陽在九歌出版的著作可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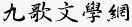
|
|
 .................................
|
向陽工坊
向陽詩房
|

|
|
|
|
|
姓氏不明
|
向陽

|
|
|
|
|
《中外文學》二月號推出「分歧的意識」專輯,刊出了我的一首詩〈我的姓氏〉。這首詩寫於九八年年末,是應專輯編輯全成兄之邀而寫的,邀稿函大意是該刊將製作專輯,要我用詩來表現台灣島上意識與認同的分歧狀態。
這樣的詩稿,是要用崩雲來表詭譎、用亂石來寫動盪,用詩來談論現實議題,用文學來風喻政治,難寫之極。我從一九八二年進入報界之後,文學與政治就像亂石崩雲一樣,難分難捨。在威權年代的檢肅之中,寫作以及編輯副刊,都帶著高度的政治警覺,一方面警覺政治的窺覷文學,一方面也警覺文學的刺諷政治,猶如走鋼索者,不時得衡量如何在檢肅中潛行偷渡、在偷渡中提防檢肅。但即使如此,還是有橫遭檢肅的時候,那些惡夢已經隨著清晨化為無形;八七年解嚴之後,我由文學人轉為新聞人,編報、撰寫社論,政治成為正餐,文學猶若點心,在實際的政治觀察中,更加了然台灣政治的綜理一切,十二年來每週至少寫一篇社論,未嘗間斷。這將近二個年代的歷程,使我深刻體會到意識型態與認同問題在當代台灣的錯綜複雜,絕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況乎詩。
但是,我還是勉力把這首詩完成了;除了寄給《中外文學》,也在我的網站「向陽工坊」發表。以「我的姓氏」為題,我虛擬了叫做「A-Wu」的西拉雅平埔族人,一六二四年誕生於南台灣廣闊的平野中,歷經荷蘭、明鄭與大清統治,他的名字由呼音「A-Wu」一路被命名為「阿宇」、到被清帝賜姓「潘」名「亞宇」為止,除了父母所賜的「A-Wu」以外,其他的名字都是得自異族統治者。「A-Wu」童年時曾經迷路在麋鹿成群的的群山,目睹荷蘭士兵進入台窩灣,十二歲時接受荷蘭傳教士教育,學習用羅馬字拼音的西拉雅語閱讀聖經;到了一六六二年三十八歲時,明鄭來台,他開始擁有漢人的名,用於「番契」之上,以便讓「我耕種的土地,我童年的記憶」都「紙一樣被撕掉」;一六八四年,六十歲的老人「A-Wu」已經習慣使用河洛話,會查康熙字典,擁有皇帝御賜的「潘」姓,這時才搞清楚此際他叫「潘亞宇」,童年時叫「A-Wu」,壯年時叫「阿宇」,在油燈點亮的夜裡。
命名的權力,不在「A-Wu」以及與他一樣的族人的手中,導致的認同的失落與悲哀,即使到了「A-Wu」過世後三百年的今天依然存在,在這首詩的第四節,我用台灣人習俗的公媽廳來擺置,「A-Wu」來到「潘公亞宇」與其牽手「潘媽劉氏」的神主牌前,看到唐山裝扮的他被掛在廳堂牆上,成為祖籍河南的來台開基祖;廳堂中子孫依序上香祭拜,年老的「潘亞宇」用他聽不懂的日本話、中年的「阿宇」用他聽不懂的中國話、年輕的「A-Wu」用他聽不懂的番仔話﹝英文﹞,沒有一個人使用他三百年來連夢中也沒有忘掉過的西拉雅母語和他說話。
「這是我嗎?」通過「A-Wu」三百年後的回憶與當下的疑惑,認同沒有解答,意識繼續分歧。台灣的集體回憶,依然像「A-Wu」誕生在這塊島嶼之際野草高聳,儘管當年的麋鹿今已瀕臨絕跡,「A-Wu」繼續迷路,在已經難以真確辨明﹝辯名﹞「我的姓氏」的大年代之中,認同就像回風吹過的干芒那樣,灰白苦澀。
「這是我嗎?」,三四百年後的台灣,這樣的「姓氏不明」的困惑繼續存在。我在完成這首詩虛擬的詩作之後,對於久無詩作的自己,能夠順利轉化政治議題為文學徵象,從「A-Wu」的生命史中隱喻當代台灣的政治乃至文化認同的不確定感,老實說有著雕蟲小試的快感;從網路上的回應來看,似乎也訴說著這首詩的感應力量。但是今夜,在燈火漸暗的夜裡,重讀發表在《中外文學》的〈我的姓氏〉,我忽然感覺「A-Wu」彷彿就在燈光照不到的暗處,問我:你寫的是我嗎?而不敢確定這樣的書寫,是在填補我自以為是的認同的隙縫?或者,是在強化隙縫的認同?在這野草高聳的歷史與文化的群山之中,在文學與政治弔詭的對話文本之內,我何嘗不也和「A-Wu」一樣,姓氏,不明。
──1999.02.19.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3年9月,《暗中流動的符碼》再版改封面,易書名為《為自己點盞小燈》。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