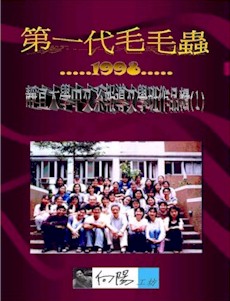|
|
||
|
《第一代毛毛蟲》序
向陽
蟬聲鳴唱的清晨,我在靜宜大學中文系開的「報導文學」課程即將結束。從去年九月開課以來,每個禮拜五早上八點二十分開始,在文學院的課堂上,我陪伴著五十多位修習這門課的學生,閱讀、討論、講授、辯難,如斯一個學年即將過去。 課室之外,一大片晴空傾斜下來,彷彿也傾著頭探向這個課堂;窗戶外面,除了晴空的臉容之外,還有悠遊的浮雲,以及壓過我的聲音,吵雜卻也令人感到悅耳的蟬聲,時歇時起,時強時弱。一個學年的報導文學課程,好快,就將這樣地過去。 面對著對我來說其實負擔過重的一大票學生,想到這一個學年來,與他們一起研討台灣報導文學的文獻、佳作,以及為他們剖析報導文學寫作技法、旨趣與美學的種種,內心不禁浮起這整個學年授課的種種畫面。這些畫面,有些清晰得連紋理都可辨析;有些模糊渙散,像水漬淌過剛剛列印出來的講義一般;有些若即若離,彷似焦距尚未調妥的快門;有些則是色調鮮明,與雨後逗留在在花瓣上的水珠一樣明亮。它們以清晨的藍天為底板,浮現在當我把眼睛拋向窗外的時刻。 在靜宜大學開「報導文學」的課,於我是相當新鮮的經驗。對中文系的學生而言,報導文學與詩、散文、小說等一樣,都屬於非理論的創作課程,通過採訪、調查、觀察以及資料的爬梳、印象或體悟的整理,把令他們感動的人事物加以寫出,大概就是報導文學了。剛開課時,問學生「為什麼修這門課」?「心目中的報導文學是什麼?」有些學生回答為了將來自助旅行時可以做些旅遊報導,有的學生則把報導文學當成新聞採訪寫作。我一點也不敢笑他們,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就連某些新聞學者的著作也把報導文學當成「新聞」文學看待。 但是,於我來說,以一個曾經長年在新聞媒體工作的文學創作者來看,報導文學一點也不會是「新聞」、新聞一點也不可能「文學」,錯誤其實來自「報導」和「文學」思辯的不足。於是,在我的教書過程中,和我所指定的多半來自新聞學界的教材抗衡、論辯的新鮮教學經驗從此展開。第一個學期,我指定了多篇有關報導文學發展過程、理論基礎的文獻,以及台灣報導文學家實踐出來的佳作,要求學生每堂課前研讀並撰寫讀後報告,上課進行討論、省思。這些文獻有當代報導文學界的視野、有來自新聞學界的觀點,有由中國古典文學探緣報導文學的根柢、有援引西方「新新聞」寫作的理論與實務。視角不同,觀點互異,相互矛盾、杆格自多。學生每週研讀、比較,通過討論、辯難,釐清報導文學的定義和定位,便成了我的功課與責任。 於是,上個學期,幾乎每週批改五十餘篇報告,就是我凌晨的夜課;針對理論與實踐的差距提出分析、提供批判思考,就是我清晨的早課。我希望帶領學生走入幽深的報導文學花圃中尋訪,迷失、迷惑,最後找到各自的出口。到了下個學期,我嘗試把這樣的追尋連結到實際的寫作中。我給學生一個學期的時間,要求他們到人群中、到部落裡、到山巔海隅,選擇題材、釐定計劃,探出頭去,把雙腳和眼睛踩到大地上,探勘、採擷、訪問、接觸、觀察乃至生活,再回到書桌寫下這些聞見行思。 匆匆地,一個學年就這樣過去。蟬聲初唱,檢驗成果的時刻已到。這一兩個禮拜以來,學生們開始交出作品,並組了編委會準備把作品結集成書。在不眠的夜裡,我逐一細閱他們花費無數體力、心血的作品,突然生出不忍的感覺。從對報導文學懵懂無知,到寫出洋溢著青春與熱血的作品,這一群學生大概也與我一樣受盡苦頭。當編委會的學生在我的研究室中,投票決定把這本作品集名為「第一代毛毛蟲」時,我知道,他們也許在暗示修這門課的苦行樣貌。 又有什麼關係呢?毛毛蟲總有展翅飛翔的時刻,蟬聲已在鳴叫,藍天正傾斜著向著更敻遠的遠方舖展過去。
──1998.06.05.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
在不眠的夜裡,我逐一細閱他們花費無數體力、心血的作品,突然生出不忍的感覺。從對報導文學懵懂無知,到寫出洋溢著青春與熱血的作品,這一群學生大概也與我一樣受盡苦頭。當編委會的學生在我的研究室中,投票決定把這本作品集名為「第一代毛毛蟲」時,我知道,他們也許在暗示修這門課的苦行樣貌。 又有什麼關係呢?毛毛蟲總有展翅飛翔的時刻,蟬聲已在鳴叫,藍天正傾斜著向著更敻遠的遠方舖展過去。
|